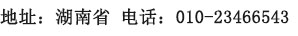年,
蟒国剧团首部作品《失忆症·蟒国》
在正乙祠古戏楼惊艳上演。
今年,
蟒国剧团新作《年轮怪》
将在12月与大家见面。
“年轮怪”的到来,是建立在一切被留存的事物、思想不断囤积之时,所谓“怪”者,也是存在于这种不断的囤积所带来的灾难之中。
当短暂建立的一致性迅速破裂后,故事中的三兄弟准备离开森林:鼹鼠去追寻月亮,啄木鸟去追寻远方的爱,兔子则希望再回到从前……
蟒国剧团导演:新戏《年轮怪》要怎么排
○李熟了
年,我们剧团排了《失忆症·蟒国》。那个戏在剧本、表演、导演、舞美上都有不少属于我们自己剧团的独特的探索,而且也很追求观赏性,在探索和可看性上尽量找到平衡点。今年我们开始做新戏《年轮怪》,在上个戏的基础上,有一些东西是全新提出的,也有一些的东西是沿着之前找到的方向继续发展。
《年轮怪》这个戏, 的排练难度首先是剧本提出来的。剧本讲的是森林里的几个小动物的故事,但是故事又是成人化的,他们一直在喝酒,醉死梦生之间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彼此的关系也经历了很多次变化。剧本用这样的题材,作了很多社会和哲学层面的思考,主题很深而且很丰富。这就面临两个问题: ,小动物形象、以及小动物行为的场面,这些该怎么呈现?对动物作一般化的拟形是肯定不行的,导表演要怎么处理?第二,这么深和复杂的主题,要怎么传达出来,才能既不丢失剧本的深刻,又让观众觉得戏好看?我们肯定是拒绝做一个说理性或者图解概念的东西,那要传达复杂主题的前提下,如何让观众看懂和觉得好看?
先说后一个问题。在解决“好懂”和“深刻”的矛盾上,我还是决定从剧本本身出发。剧本本身是解决了这个矛盾的。剧本首先写了一个清晰和起伏的故事,然后把深刻的、主题相关的东西都埋到剧情里去,用剧情的各个部分去隐喻这个主题, 完成表达。那其实导演 步该做的,就还是先把剧情排明白。
排明白剧情,这是中国观众最容易接受的,能把故事看懂,很多人就会有一个起码的“这戏我看懂了”的感觉,表达都是从里面再去体会的。但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同一个人物,同一段台词,可以有几十种解释,而不同的解释会把对于剧本的剧情解读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在这里,我没有什么花哨的技巧或者新技能,依然是运用的是导演专业最为基础的事件和行动的分析方法——去把剧本划分成若干个舞台事件,不同事件之间缕清楚人物的舞台行动。这个方法虽然传统,但是对于建立演出结构极其有效,能让我们清晰的知道每一个角色到底在干什么,到底为什么说那么一句话。一旦这个分析清楚了,演员演得也有信心,因为心里是充实的;观众看得也放心,起码不会跟不上剧情。台上台下都踏实了,我们再用各种手段去做进一步的主题阐释,也就有底子了。
除了用这个方法排明白剧情的发展和结构,中国戏曲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阿甲先生在讲戏曲表演时说,中国观众的习惯是不爱去猜剧情怎么发展的,更愿意一开始就都知道了,但是看你怎么展开,怎么表现,所以一出戏可以反复演,观众对剧情烂熟于心了也看不厌。相应的,演员上台会自报家门,演出中会和观众交流说内心独白,用各种手段提前告诉你我怎么想的、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不让人物到底要干什么成为观众看戏时要去理解的一个障碍。参考这个逻辑,《年轮怪》里也会在人物的某段行动刚开始时,就给出一些有暗示性或者指示性的调度或者造型,把他这一场的行动目的都交代出来。但是也不会像戏曲报家门那么直接,也还是想半遮半掩,留一点隐喻的美学气质。这个想法还比较初期,还待实验。
“好懂”解决了,就是“深刻”的问题了。前面也说了,剧本本身把主题埋到了剧情里,其实只要能把剧情排清楚,深刻性自然就是有的。所以对于导演,就不是如何传达深刻的问题,而是如何强化深刻的问题。这里我主要是通过一些有象征意味的调度和造型去让观众产生联想的欲望,只要观众看了,觉得这个造型或者调度应该是有某种表达的,愿意去想一想,目的就达到了,解读成什么样就是观众的自由了。这个方法在上个戏里用过,尤其在上半部的《失忆症》里,我一直用一个作为道具的圈在制造象征符号,好几次演后谈都有观众问这个是什么表达,那应该说这个方法还是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但在这个戏里,这种符号的创造可能会多很多,一旦象征性的构图多到一定量,整个戏的美学气质就也更丰富了。当然,前提都是要把剧情排明白,象征性的构图只能是一个辅助手段,去对一些重要的子主题做一下点送,不能把整个戏搞成符号迷宫了,那就本末倒置了。
《失忆症》剧照?
再说回最初的问题,小动物形象,到底该怎么呈现?演员怎么演呢?自然主义地模仿动物,无疑是庸俗的;去把动物的东西夸张化,又会像是儿童剧。在这里,梅兰芳先生的一个观点对我启发特别大。梅先生谈戏曲里的孙悟空形象时说,演得好的,出场就让人觉得是一个神,一个英雄,霞光万丈,然后再加入一些猴子的细节作为表演补充,而演得不好的,极尽模仿猴子各种生活细节,却只让人觉得厌烦,丝毫不是孙悟空该有的形象。梅先生真不愧是大师!其实只要在戏剧里表演,不管你的角色是人是动物、是神是*,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人物形象,首先还得把是这个角色当角色本身看。所以这个戏里,我们让演员首先不用考虑这是动物,就是人物,你们人物是什么样的,把这个演明白,然后我们再加一些动物元素作为点缀放进去。毕竟能打动观众的,不是你多像某种动物,再像又能怎样呢?但一旦人物立起来,情感也是真实的,观众就会看进去,而不管想让观众共情还是思索,只要他没在玩手机,一直盯着你戏看呢,那可能性就都是有的。
△《失忆症·蟒国》中董畅饰演“蛇”
在表演动物上,除了这个大原则,还有一个新的东西是这次想实验的。张庚先生在为戏曲改革做摸索时,提过一个尝试可能,可惜未能延续。他提到说,戏曲演员在塑造人物时,经常对一个动物“取形”,这个“取形”不是去模拟外形,而是用这个动物的节奏去创造人物。比如《十五贯》里的娄阿鼠取一个老鼠的“形”,节奏就是随机应变、伺机溜走,因此坐立不安、反应极快;而《时迁偷鸡》里时迁取一个壁虎的“形”,就是停时毫无声息、动起来极为麻利,连道白都迅速短促、不带尾音。放到我们这个戏里,正好演的就是动物本身,如果从节奏上取一个所扮演的动物的“形”,应该说是不冲突的。这个方法如果能够实验成功,也许对于未来舞台上的人物塑造也能开拓出一点新技巧来。
《年轮怪》里,除了用什么手段去演小动物这个特殊的课题,也有从《失忆症·蟒国》里延续而来的一以贯之的表演方法,是我觉得在各个题材的戏里都可以通用,同时也需要经过多个剧目来长期实验的。对《失忆症·蟒国》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那个戏里在表演上最核心的是两个概念,都是我们自己提的,一个是舞台动作的“去日常化”,一个是让演员通过重心控制去产生“能量”。
前一个概念是对于当代戏剧表演如何学习戏曲的这个思考,目前我们得出的结论。现在有不少戏,一说“民族化”,一说学戏曲,就是把戏曲现成的身段、动作放到话剧里来。这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粗暴的。戏曲本身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有机结构,身段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放到那样的声腔体制、那样的脚色行当体制里在演,它才是成立的,也才是鲜活的。这些都是一个整体。单截几个身段出来,既是破坏戏曲,也是融不进当代戏剧里去的。那当代戏剧表演能怎么学习戏曲呢?“去日常化”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可能性。具体到我们戏里,就是台上不能出现任何生活化的动作,所有移动步法、手势手型,都要是经过设计的,并且设计结果必须区分于日常。这个应该说不单是从中国戏曲里来的特征,整个东方戏剧,像日本的能剧、歌舞伎、狂言,也都是这样的。但同时,我们“去日常化”的动作设计也要规避戏曲动作,不能是做一个所谓“戏曲范儿”的戏,而是用“去日常化”作为基本原则,来重建一套动作方式。
后一个演员“能量”的问题,是从我对中国戏曲、铃木忠志训练、欧丁剧院训练的研究里来的。上一个戏排练时,我们就基于这些,开始创造自己剧团的演员训练法。经过上个戏的实践和一些思考,很多概念更加明晰起来。我突然明白,所谓“能量”,听起来很虚,其实就是一个基础物理原理:你发力(做功),自然就制造出来了能量;但是能量产生后如果不加以控制,也就直接又消耗出去了,所以把它控制在自己身上,才能转化为表演中所使用的演员“能量”。总结来讲,制造舞台上的演员“能量”其实很简单, ,持续发力,第二,把这个力完全控制在自己身上。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完善了自己的训练方法:要求演员首先保持住腰部重心的平衡,然后在全剧中始终从腰部重心持续向上下前后四个方向发力,完成能量的制作和基本控制;同时配合以大量干扰和冲击平衡的动作,即所谓“ 的平衡”,去让已经被制造出的能量需要被更强的控制,使能量得到增强。同时,又以心理现实主义的心理技巧去建立人物,让《年轮怪》中的表演始动于能量、而归依于人物。
△《失忆症·蟒国》剧照
除了这些,还有像舞台调度上学习戏曲的空间调度、建立“折叠空间”,舞美上要“美术”、不要“视觉”,以及许多具体形式上的想法,由于篇幅所限,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更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