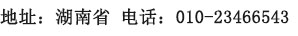每个女人心中都住着一只“黑坤包”
——《铆钉蝙蝠黑坤包》创作谈
郊庙
小说收尾处有句话,“每个女人心中都住着一只铆钉蝙蝠黑坤包”,我毫不讳言就是拙作的文眼。小说与人一样,是有血有肉有骨架的鲜活存在,同样有“眼睛”。眼睛是人类与世界交往的窗口,眼睛会出卖人,你捕捉住了文眼,就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了这篇小说。小说有两条线交替穿行,陈晓与蔡长虹,“我”和麻德诚。但小说从 人称“我”的视觉出发,两条线靠“我”串联。泛泛而言,“黑坤包”指向女人的猜疑之心,有了猜疑之心,势必去求证。结果呢,过着浑浑噩噩、貌似幸福日子的“我”洞悉了可怕的真相,而把我带下水的陈晓在收获梦寐以求的真相的同时,却同时收获了一度失落的甜蜜(那甜蜜其实从未失去过,只不过她自以为失去过)。黑坤包是个啥东东?首先,它是一个具象物,陈晓敝帚自珍般地隐秘地“保管”着(所有权不归于她),“我”也亲手摸过、捏过;其次,它还是一个含义暧昧的象征物,既代表着女性(或泛指人类)的猜疑心,也暗指一切能激荡你四平八稳生活的来历不明物,有时它还会变换面目,比如“我”在麻德诚车里找到的杜蕾斯。
我的最初设想只有一条线,就是陈晓与蔡长虹,但从“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我”只是冷静的旁观者。如此,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暖人故事,正能量,主旋律。但正如我在小说里写下的那句话,“有时只是幻象,有时却未必”,岁月静好对更多的人来说只能是奢望,比如“我”。于是我就设想构筑两条平行线,小说之弦和人生步轨要向不同的两个方向延伸,增强小说张力,丰满小说意涵。犹如满弦的弓,箭矢飞出去了,戳中了真相靶心,小说就该结尾了。哪怕伤痕累累,亦属预料之中,是获悉真相后必须承受的代价。从这个角度说,本小说有点观念先行的意味,要写这样的东西,才去构思具体故事,而且事先决定了我要写出“这样的几个角色”。
但是,具体到两个女人同样对自己的男人起了疑心的情节构思上,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支撑物,就是那如同天外来物的黑坤包。它勾起了陈晓的猜疑,进而勾起了“我”的猜疑,简直有点儿审美移情。“我”本只是受人所托,却“临时起意”把麻德诚也作为“对象”交代给了浩哥。临时起意是无疑的,可以肯定“我”此前并无此番打算,一方面,或许是受眼前场面的启发,可以帮得上忙的人(浩哥)就坐在眼前,唾手可得;另一方面,“或许那时我就已在考虑了,早点儿参与其中也好,如果我已面临与陈晓同样的处境,我为什么还要傻乎乎地独善其身呢,我站在十字路口却没有红绿灯,总得找一条出路”。也就是说,对麻德诚的种种不轨,“我”潜意识里早有疑虑,只不过被“我”清醒的意识死死压制。“世上本无事,何必惹尘埃”,在陈晓的黑坤包事件点醒“我”之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我不愿往那个方向联想,清醒的意识总是提醒我要趋利避害,何必和无凭无据的事较真呢”。陈晓的黑坤包犹如一把火苗,点燃了“我”胸中的猜疑之火,从此“我”的人生毫无意外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体现在文本上,小说就变成了两条线,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和陈晓,十四中的一对好闺蜜,从此犹如霄壤,一个飞上枝头做公主,一个虎落平阳被犬欺。陈晓说,“毛毛,我只需要真相”,而且是吐词清晰;或者如“我”在浩哥面前所说的,“我们的确只需要真相,其他的倒在其次”。的确,获悉真相后的结局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获悉真相。
小说当然也可以第三人称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叙述上可以做到更客观、冷静,我甚至也设想过以毛毛和陈晓两个“我”的 人称切换交替推进。这就涉及到小说人称和叙述视觉的问题。几年写作,这是我 次以“我”指称女性人物,算是尝试,成功与否交代读者去评判。以前不用“我”指称女性人物,是自我误导,以为“我”若是女性呢,总得对女性的身体和心思如同对自己的身体和心思那么了解,这一点在一二十年前几位风头强劲的美女作家作品里体现得酣畅淋漓,我不评判有些评论家说她们是在用身体写作的观点,但我想,我怎可东施效颦呢,性别错位意识对我有什么好处,起码我比不上人家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信手拈来啊。写过这篇小说后,我的看法是,我想多了。撇开性别意识,总体来说,采用 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我没有特别的倾向,用活了都好,写作伊始便公平对待“我”和“他”(或“她”),至于彼此数量,从没有统计过,无聊。村上春树说他用“我”写了头二十年,其后小说的篇幅与架构扩展开去,才不得不用第三人称。这一点我赞同,一般而言,篇幅较长的采用第三人称会更适宜,我几个待字闺中的长篇都是第三人称,它们耗费了我这些年更多的生命能量。
我不擅长写创作谈,唠叨这么多,也不知说明白了些啥。总认为,把作品交到读者手里,作者就该隐居幕后,不方便再在台上胡言乱语。当代的西方解构主义批评,宣称“作者死了”,因为他们认为作者能否在文学文本中准确、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颇值得怀疑。我想我也一样,我把黑坤包的事说清楚了吗?估计未必。即便我想清楚了要在小说里写些什么,但语言完全达义永远不可能。这个意义上,我承认“我死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也是使用语言符号进行的,那么批评家能否言达其意也颇值得怀疑,何况如果是针对异文化下的作品进行批评呢,就更多了一层障碍,可见“批评家死了”也成立。但读者不会死,小说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读者来深化和拓展,小说借以读者的阅读而延续生命,一千个读者会读出一千个“毛毛”和“晓晓”。
感谢读者,感谢《啄木鸟》提供作者和读者相会的鹊桥。
作者
简介
郊庙,浙江温州人。工作之余从事小说写作,兼写评论。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思南文学选刊》《啄木鸟》《中国作家》《钟山》等。
精彩回顾
《铆钉蝙蝠黑坤包》,载《啄木鸟》年第5期
延伸阅读
《啄木鸟》年第5期
定价:15.00元
订阅方式
方式一:《啄木鸟》微店订阅
扫描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