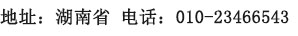贴梗海棠
那天在望江楼公园,见到生平可称之为“幽篁”的竹子。
王维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所谓幽篁,小时候在语文课本中对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密密竹林中雾霭弥漫,其中的竹子已长出幽寂气韵。在这以前,现实中没有见过这般称得上“幽篁”的竹子。
生在西南,常见竹林。乡村家家户户喜种竹子,房前屋后无不是一片翠竹,竹林下盖着一间青瓦泥墙老屋,是四川乡下常见的风景。自父亲结婚,和几个兄妹分家,同母亲移居到村里一处高地上,兴建房屋,并在房前屋后分种两窝慈竹,一棵山桃。十年后,我出生,两窝竹子已长成两片竹林,前后抱住我们家。所以印象中,卧室的窗户框住了一片四季如常的绿,阳光好的时候,这片绿带着闪闪金光,阴雨天时,它暗成一片墨绿。墨绿和闪光伴着我的梦,从童年到少年。
至今,回想起约摸五岁的光景:母亲在堂屋里纳鞋底,我穿着她缝制的一件厚棉花的梅花青底棉袄,戴一顶毛线虎耳帽,站在屋檐下望着院坝边缘茂茂的竹林。看风从竹林经过,哗哗哗。听狗毛雨打在竹林里,沙沙沙。下了一夜大雪的竹林,积雪把竹子压断,噼噼啪啪,将睡在阁楼上的我惊醒。更多时候,独自在竹荫下的院坝中看蚂蚁搬运虫子。时而捡起一片笋衣,用灶里抽出的炭火点着,看它背面那片痒手的毛呼哧一下滚过一层火。
门口那棵山桃已和竹林长成一片,粗壮树干从竹林中斜斜探出,横亘在路旁排雨渠的石头小桥上。春天,披散的桃枝开满粉红桃花,我们喜欢爬到树上坐在花荫里,觉得快乐。夏初,坐在树上吃它结的桃子,看树下奔流小溪,父亲用一张网堵在水口,捉来一桶桶虾蟹、鱼鳝。夜里,天气闷热难耐,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月华如水,院坝似变成一方浅浅的水池,竹枝投下影子,叶片若细长小鱼。风吹时,竹叶微动,仿佛一群小鱼在池水中也动起来。我躺在竹席上,听远山传来鹰鹃幽怨而悲愤的啼鸣。至夜深,天空下起夜露,月亮被包裹成一枚长毛的的蛋*,我们才收拾好去屋里睡觉。
父亲念过一些书,但不知道屋前种竹有何寓意。乡人图吉利,竹子节节高升,或许也是这般世俗的意思。只是母亲常抱怨,因为竹子长得旺盛,一刮风便簌簌落下枯竹叶,刚刚清扫干净的院子,又一片狼藉。春末,新笋拔节,很快成树,笋衣干透,也纷纷随风剥落下来。我却喜欢这种时刻。往往是傍晚或清晨,太阳斜射,竹林刚刚从晨雾和暮霭中醒来,叶片上洇出露水,跳动一粒粒刺眼钻光。晨风鼓动时,竹叶簌簌,竹子活动它的筋骨,发出嘎嘎或哒哒哒的声音,一边抖落身上万千的细屑。在风中滚动的落叶,旋转着落在我头发上、肩膀上,干枯的大片笋衣,是滑翔的飞船。毛虫椭圆的蛹壳,斑鸠的旧巢,一一跌落。我在这场“杂物雨”中得着各种新奇的玩意。这时候的竹林,令人沉迷。有时啄木鸟躲在深处捉虫,嘟嘟嘟嘟嘟,五声为一组,节律性地敲击着。王家的婆婆害怕这种声音,向我母亲说,她屋后竹林里有人在敲,是她男人要回来找她了。
她的丈夫去世多年,墓在竹林下。因为邻居都已搬去城里,她独自住在山下一隅,又罹患糖尿病青光眼而不能睹物,面对墙倒瓦落的破败土屋,屋后竹林也尤为幽寂。老人思念故去的伴侣,夜里托梦,山里的声音自然容易入梦。这些年回乡,一路都听见啄木鸟在竹林中发出阵阵啄木声。至春末杏*时,我们在干田里点花生,噪鹃的“*哭”声凄厉而不绝,母亲也总说,鸟叫得阴森吓人。我听着,倒觉得颇新鲜有趣。小学时对古诗文中“老树昏鸦”的描写神往,但川中地带从不见乌鸦,现在,噪鹃倒是提供了这样的景致。只是不同于乌鸦啊啊地叫,是形同人受到突然的惊吓,而是呜呜地哭着,更显凄楚悲凉。啄木鸟和噪鹃是退耕还林*策实行十数年后新来的鸟,儿时并不怎么见过。
一只斑鸠
这次在公园,见到如此繁茂的竹林,因此想起家乡的竹子,童年的幻梦。
那天傍晚,走到园中一片坭竹林里,看见一窝窝竹子从发白的泥土中伸出,像一缕缕密密的头发,竹梢从天空披散而下,围拢而成自然的天井。天光落入井中,打在光洁的泥地中央,愈发白而光亮,仿佛面对一汪清浅的水。曾经没有离乡的夏夜,也见到这样亮而静谧的竹荫下的“池塘”。我坐在竹下的木椅上,四下无人,暮色低垂,慢慢将我包围。于是突然想到那句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月山行
四季风物·草木鱼虫·自然笔记
月山行